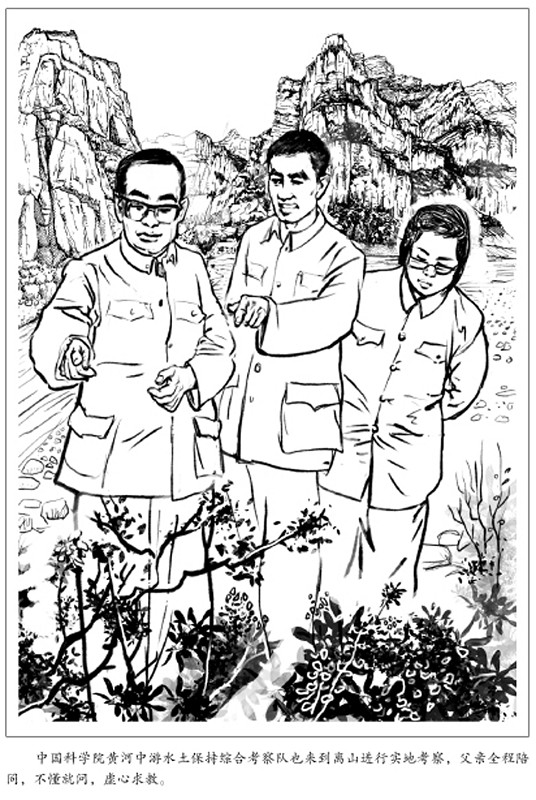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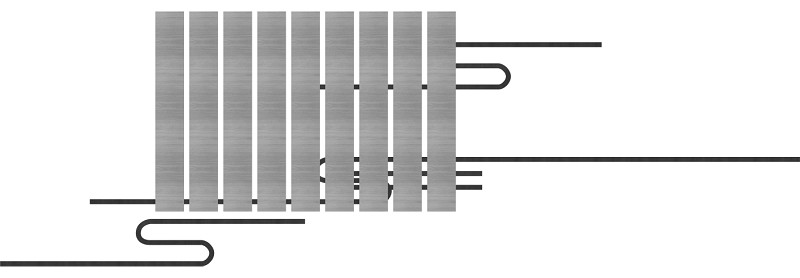
山西临县人。1945年3月参加工作,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5年3月至1956年8月,先后任方山县教员,县政府文教科科员、科长,县委宣传部部长、副书记以及离山(今离石、方山、柳林)县委代书记;1956年8月至1975年4月,先后任交城、和顺、汾阳、临猗、洪洞县委书记;1975年5月至1979年11月,任中共临汾地委副书记;1979年12月至1985年12月,任中共忻州地委、行署副书记、专员;1986年1月至1994年,任忻州地区人大联络组组长、人大工委主任。1994年离休。
讲述人:刘建平 讲述时间:2022年8月23日 整理人:孟志平
“平台是党组织搭建起来的”
我的父亲刘耀于1925年出生在吕梁山区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,幼时在村里念书。我不太清楚父亲念书的时候是不是聪明伶俐,但从父亲同事和朋友的回忆中得知,父亲对学习有股子钻研劲,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时代,父亲一有闲暇就钻进书堆,读书成为他的一种习惯。追寻父亲生前轨迹,我发现父亲的读书经历非常丰富。他八九岁时开始在村里的学堂念书,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,1938年,他就进入一所党领导下的、由牺盟会创办的高级小学,开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。大概在1941年,他又进入党创办的晋绥边区第一中学学习。而他参加革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当小学教员。父亲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,所以他常说:“我是党的儿子。”
父亲在他人生的成长前期一直都在学习,也恰恰是那种难能可贵的学习经历成就了他最高光时刻——日后他的一篇文章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。
1950年代,父亲任离山县委副书记。当时,省里首次召开水土保持工作会议,提出要全面开展综合性的水土保持工作。1955年,山西省水土保持工作局在离山县建立了一个水土保持试验站,对当地流域的降雨、径流、泥沙等情况进行观察。当时,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也来到离山进行实地考察,父亲全程陪同,不懂就问,虚心求教。由此,他产生了一个想法,在全县范围搞一个规划,抓住当时迅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契机,改变单家独户自发治理的做法,依靠组织综合力量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工作。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通力合作下,经多方调查研究,父亲撰写出了《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工作》一文。
这个规划先是报到了地委,接着又报到了省委。让父亲没想到的是,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文章,亲自把标题改为《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》,并加附了一段长达二百六十字的评语。其中第一句就是:这是一篇好文章。
那年,父亲才三十岁。
可以想见啊,父亲有多么激动。他一直把这段批语视为一种鞭策,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,不管遇到什么挫折,心里头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就会涌荡出来,激励他度过了一次次人生困境。
父亲在晚年和我们子女聊起这件事时,他脸色红润,激动难抑,就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,又回到了那段让他终生难忘的年轻岁月。父亲总是把那段经历视作他的人生奇遇,实际上在我看来,它不是奇遇,而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。你想啊,那个年代,在战争中,能够静下来念书的人并不多,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,识字断字的都屈指可数啊!父亲不光念了好几年书,还当过教员,也就是说,正是前期的读书教书岁月为他打好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对这件事,父亲还有个自我总结。他说:“平台是党组织搭建起来的……这辈子能得到他老人家的指示,没憾。”
“这已经好很多了”
父亲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这样评价父亲:一生廉洁自律、生活俭朴、以身作则,堪为表率。
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,父亲在忻州当专员时,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,可他仍然布衣蔬食,不吸烟也不喝酒,生活非常简单。
父亲下乡调研,若吃饭时见饭桌上摆着酒,他就会站起来把酒拿掉,只让炒盘土豆丝、豆腐,最多再加个炒鸡蛋。别人有点过意不去,父亲就说:“这已经好很多了!”有时父亲下乡回来,机关食堂已经关了门,父亲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家里吃饭,母亲也习惯了,常常给做拉面,切一点儿蒜薹倒点酱油拌到面里,就是一顿饭。
有一年,为了让孙子、外孙都吃上鸡蛋,母亲想养几只母鸡,父亲便托人找养鸡专业户去买四只快产蛋的小母鸡,专业户要了十块钱。父亲得知后,认为给的钱少了,硬是又拿出十元钱交给对方。
1979年,父亲和同事去广州参加广交会,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晚上,他们实在找不到价格合适的住处,就在一个澡堂子里住了一夜。
1980年,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党员改进作风问题。地委决定,在地区开会时领导同志不坐车,全部步行。父亲第一个严格遵守,每次都是步行近一里地到当时的地区招待所参会。即使下雨或下雪,司机把车都开到门口了,他也坚持不坐。有时吕梁老家的亲戚到忻县看他,他都是安排大家在家里吃住,没有去过招待所。家里有亲戚想让他给找个工作,他都婉言拒绝了。尽管自己也困难,但他仍要给人家一点儿钱,安顿人家回去好好劳动生产。
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很多,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太好理解,但这都是事实。在那个年代,父亲他们那一代领导干部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
父亲在工作中淡泊名利、待人宽厚,他处事通透是出了名的。他在忻县地区担任专员期间,有位省委领导到忻县调研,接触了不少当地的干部群众,见大家对父亲的评价很高,省委领导非常满意,就提出让父亲到另一个地区担任地委书记。父亲说自己年龄大了,对忻县的情况也熟悉了,谋划下好多事情还没办完,就留在忻县当专员吧。
“一辈子相夫教子吧”
上面这句话是父亲斩钉截铁说出来的,但父亲没想到这却成了他和母亲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墙,也成了他和母亲之间一辈子的隐痛。
在外人眼里,母亲就是一位和蔼可亲、不急不躁的家庭妇女,但我们都知道,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,她把她的后半生和前途都贴了进去。
20世纪60年代,正是国家困难时期,中央提出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要求压缩机关干部,各县都有压缩的硬指标。我母亲当时是机关工作人员,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吧。那会儿,父亲在汾阳县担任县委书记,拿着压缩指标该压缩谁啊?压缩谁你就把谁一辈子都影响了,可是不压缩这工作又完成不了。当时纪律很严,父亲是县委一把手,县委县政府多少人的眼睛都盯着他。父亲就决定从自己身上动刀子。有一天晚上,父亲下了班进了门,脸色非常严肃,几次欲言又止,踌躇了半天,终于跟母亲说:“我也只好从你身上开刀了,先把你压了算了。你回家吧,一辈子相夫教子吧。生活上你放心,我养咱们一家。”母亲沉默了一会儿,她没哭,泪都流进了心里。她说:“你实在做不下工作,从我身上做起也可以。回家就回家吧。”父亲把母亲的名字第一个报了上去。没承想,母亲单位的领导不同意,说:“人家在工作中表现得那么好,咋就让人家回家?干得不好的咋就不压?要压也得压那些不好好工作的。”父亲几次给那位领导打电话,硬把母亲从单位弄回家了。母亲就这样成了家庭妇女。母亲的牺牲太大了。
“文革”中,父亲被批斗,工资停发了有一年,家里就靠母亲一人支撑。我兄弟姐妹多,为了一家人吃饭,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难,但我没听过母亲有一句怨言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都渐渐淡忘了这件事,好像母亲从一开始就是个家庭妇女。
到了2014年,父亲因病住院。在病床上,他和我聊起了当年,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欲言又止。过了一会儿,父亲说:“哎呀,我这要是走了,家里没了收入,你妈咋生活呀?我对不住她呀!”
我这才发现,原来一向坚强的父亲一直都记着这件事,一直没放下对母亲的愧疚。当然此时,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了,母亲的生活自然不成问题。可这事是父亲藏在心底的一个解不开的疙瘩,一个半个多世纪化解不了的心病。
父亲和母亲在1942年就结了婚,他们两人是经媒人介绍认识的,两人都来自农村。母亲有着勤俭持家的好品性,她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了父亲,给了我们这个家,她付出的不只是精神层面上的,还付出了她的事业、她的前途。
后来,父亲出院回到家,我就和母亲当笑话说起这件事。母亲叹了口气,帮父亲盖了盖被子,边盖边说:“你好好养你的病吧,我又没饿着肚皮,娃娃们孝顺着呢。”母亲说完这话转过了身子,我看见母亲在悄悄抹眼泪。
2017年,父亲离世。临终前,他一直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,断断续续对母亲说:“这辈子……我……就对不起……你啊……”
母亲笑了笑,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哭了。
父亲走后,母亲对我们说:“你们几个都像父亲,一心扑在工作上,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。其实你父亲对一家人都好,没有啥对住对不住的。一辈子守着锅灶,我也乐意。”
这一次,我们笑了,母亲却哭了……
摘自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:我的红色家风》